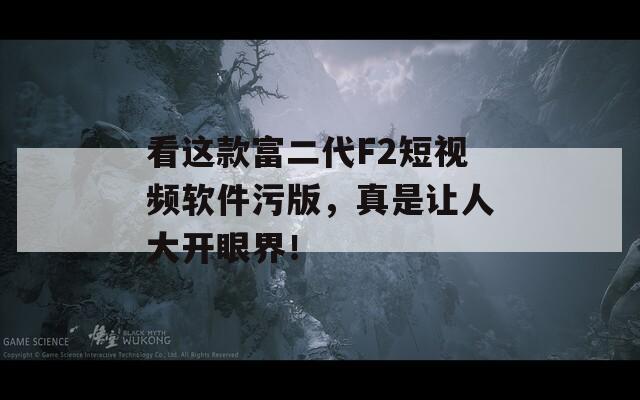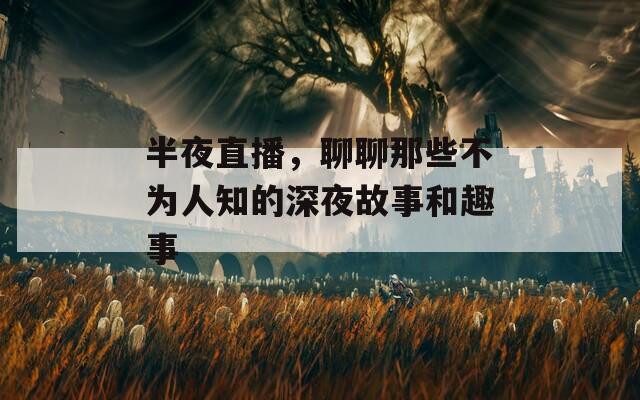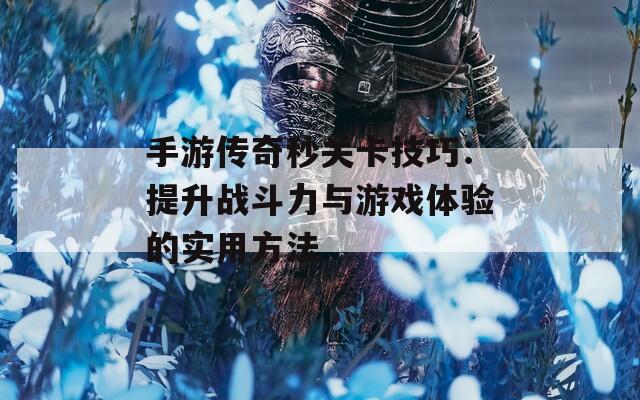楼道飘香的偶遇
搬来这个老小区整三个月,直到上周二的傍晚,我才真正认识了住斜对门的陈伯。那天刚跨进单元门,就闻到一股混着蜜糖香的肉香——不是普通叉烧甜腻得发齁的气味,是带着焦糖脆壳的油脂气息在楼道里横冲直撞,把我钉在401室门口挪不动腿。
正犹豫要不要厚着脸皮搭讪,防盗门突然"咔哒"打开。穿着深蓝围裙的老爷子端着白瓷盘出来,盘子里码着切得极薄的叉烧片,晶亮的暗红肉片半透明得能照见顶灯,刀工细得赶上日料店的刺身师傅。
颠覆认知的初体验
第一口咬下去时,我忽然理解什么叫"食过返寻味"。脆壳在齿间碎裂的声响,像踩碎秋天薄薄的冰层。肥肉部分完全不像普通叉烧会嚼出油渣感,反而像鹅肝酱般丝滑化开,瘦肉纤维早被捶打得松软却不失弹性,蜜汁竟是从肌理深处渗出来的鲜甜。
更绝的是藏在肉缝里的陈皮碎末,老广做烧腊常见的辅料,但他不知用了什么秘方,柑橘香不是浮在表面的装饰,倒像从三十年陈年老树上采来的鲜橙皮,把整块叉烧烘托出高山云雾茶的悠长尾韵。
灶台边的独门技艺
趁着第二天送还餐盘的机会,我借口"怕酱汁残留"赖在厨房。七十平的老房子里,那口三足铸铁锅像个古董似的支在煤气灶上,锅沿积着层层深褐色的焦糖层。
"二十三年零七个月啦。"陈伯摸着锅耳上的凹痕,"当年在油麻地烧腊铺掌勺,台风天被掀翻的雨棚砸出来的。"他说这话时,正用铜勺舀起自酿的荔枝蜜在肉排上画圈,深琥珀色的蜜浆遇热瞬间焦化,在叉烧表面形成细密的龟裂纹。
原来秘密藏在三次翻转里:第一次用云南岩蜜打底,第二次补广东荔枝蜜增香,最后一轮浇上自酿的梅子酒。我数着他从旧饼干盒里摸出的古早温度计,炭火要精确控制在278℃,多一度就成焦炭,少一度难出脆壳。
半条街的深夜排队
到了第三天晚上八点,我发现单元门口停满陌生车辆。开五金店的张叔端着不锈钢饭盒蹲在台阶上,见我就咧嘴笑:"老陈头每月初八开炉,半个区的老街坊都掐着日子来。"
402的阿婆递给我个保温袋:"闺女帮我捎两斤,我给住院的老头子送去。"电梯间挤满了拿着容器的人们,有个穿正装的年轻人捧着乐扣盒,腕表在楼道灯下反着光,说是从城东CBD打车过来的。
陈伯的厨房成了临时档口。他坚持用老式红白油纸包装,麻绳捆三道的动作熟练得仿佛回到三十年前的香港街头。肉香顺着通风管道飘满整栋楼,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米其林餐厅在这里开了快闪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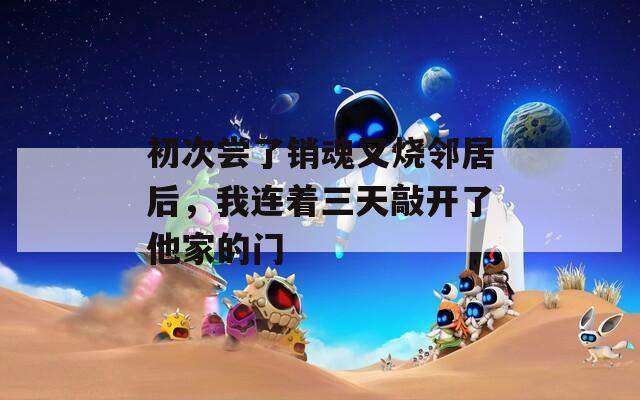
老手艺的温度
周末帮陈伯整理阁楼,翻出泛黄的报纸剪贴簿。1997年的《星岛日报》上,穿着白背心的年轻人在"全港烧腊争霸赛"的颁奖台上捧杯。照片边的备注写着:陈永年,油麻地新兴烧腊店第三代传人。
那些装在铁皮饼干盒里的温度计、发黄的食谱手札,还有被磨出凹痕的斩骨刀,突然都有了故事。陈伯说现在的年轻师傅依赖恒温烤箱,再没人肯守着炭火调风向,更不会为了观察糖色半夜定十几个闹钟。
临走时他塞给我个搪瓷缸,里面是腌了七天的叉烧头。回家煮面时切两片扔进汤里,整碗清汤瞬间染上霞光,喝一口鲜得喉咙发紧。这哪儿是调料,分明是五十年的时光熬成的味觉记忆。
邻里间的烟火传承
后来整栋楼自发搞了个"叉烧基金",各家凑钱给陈伯换了套带自动排烟的炉灶。每天傍晚五点,厨房窗口准时升起袅袅轻烟,楼下遛弯的大爷会突然加快脚步:"老陈开灶了,赶紧的!"
上周社区美食节,主办方特意把最佳摊位安排在榕树荫下。陈伯的木头推车上挂着"油麻地新兴烧腊"手写招牌,排队的人龙绕了花坛三圈。当评委尝到那口带着陈皮回甘的叉烧时,有个美食博主直接对着镜头爆了粗口:"这才叫烧腊!我之前吃的都是塑料!"
现在我微信置顶着两个群:"401叉烧预定群"和"陈师傅手工腌料团购群"。上周教陈伯用手机接龙,老爷子戴着老花镜认真研究到半夜,第二天骄傲地宣布:"以后下单满五斤送秘制酸梅酱!"